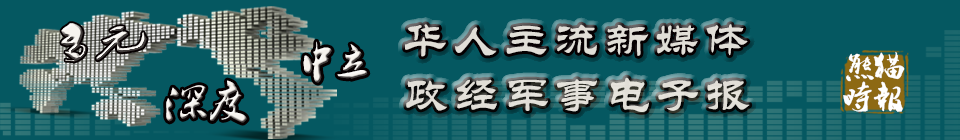【熊猫眼】英國美術史學者克格(Kenneth Clark)在60年代為英國廣播公司主持一系列名為《文明》(Civilisation)的紀錄片。其中一集內,鏡頭中克格站在塞納河畔,背着身後的巴黎聖母院,向觀眾說:「甚麼是文明?我不知道。我仍不能夠用抽象的詞語定義它。但當我見到它時我就能識辨它。」然後他轉身望向河對岸的聖母院,續說:「而我現在正看着它。」
無疑,巴黎聖母院是西方文明一顆最閃耀的瑰寶之一。這個佇立於巴黎市中心塞納河畔,樓高93米的中世紀哥德式天主教教堂,於1160年開始興建,至1345年方才建成,比起羅馬教廷的所在地,漂亮宏偉的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教堂,歷史還要長數百年。由於其為著名的巴黎地標,聖母院還漸漸成為了法國民族的身份象徵,也成為了西方文明的重要遺產。
世俗主義:政教分離的衝突與傳統
身為巴黎市內天主教的著名地標,聖母院曾於法國大革命時蒙難。當時革命分子務求將代表舊制度及舊政權,長年腐敗的天主教會從法國民族身上連根拔起,曾創立一種「理性祟拜」(Cult of Reason)的無神論宗教以取代天主教。教會掌握的大量土地、權力、財富遭到充公,聖母院首當其衝,與其他教堂一樣改成為「理性殿堂」(Temples of Reason),聖母像一度被自由女神像取代。聖母院外牆28個刻有《舊約聖經》君王的雕像,亦被誤以為法王而遭到斬首。
雖然革命分子去基督教化的行動十分激烈,不少文物更因此遭受破壞,但卻成為了法國政教分離傳統的開始。多個世紀以來天主教累積大量土地和財富,嚴格限制了人民的生活與思想,卻由聖母院遭洗劫的一刻被解放出來。自此法國厲行世俗政策(Laïcité),宗教漸漸從法國政治及社會退場,聖母院的宗教色彩亦漸漸褪色,反成了一個熱門的旅遊景點及歷史古蹟。
然而到了今天,穆斯林人口在法國持續上升,也令奉行多年的世俗政策受到挑戰。2001年911襲擊後,西方的恐伊斯蘭情緒急速升溫,法國總統希拉克2004年以推行世俗政策為由,禁止校內戴上有宗教意義的標誌,被稱為針對穆斯林的頭巾禁令,結果引發軒然大波。2010年總統薩爾科齊又通過另一項法案,禁止戴上波卡(Burqa)此類附有面罩的穆斯林服飾,結果又爆發另一場爭議。
雖然不難看出,法國政府在推行世俗政策當中,有針對穆斯林人口的意味,當中也不乏恐伊斯蘭的偏見和歧視,然而在世俗主義傳統十分強烈的法國,面對宗教人口逐漸增多,也處於兩難境地。加上原教旨主義的冒起,恐怖襲擊時有發生,又有極右的排外分子推波助瀾,更令問題變得複雜。這回聖母院失火,便遭網絡上的極右分子乘機發布假新聞,稱是穆斯林縱火。聖母院上雄雄烈火的光影中,可看出宗教與世俗主義在法國230年的鬥爭。
人文主義:鐘樓駝俠的低下層呼聲
而在巴黎聖母院火災後,不少人也回顧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在其經典名著《鐘樓駝俠》中對聖母院的描寫。事實上在19世紀時,聖母院曾一度殘破不堪,直至1831年《鐘樓駝俠》出版後,公眾才拾回對聖母院的興趣,更開始為教堂大幅修葺。今次火災中因焚毀倒塌的尖塔,便為當時所興建的。
然而《鐘樓駝俠》的主旨,除了是對聖母院這座哥德式建築為之稱頌外,也是道出主角駝背敲鐘人及吉卜賽舞者,這類庇蔭在聖母院下低下層人物的故事。雨果的另一大作《孤星淚》內的人物,也是罪犯、孤兒、工人等販夫走卒。而雨果正正是以人文主義的筆觸,借這些因樣貌奇醜而被拋棄的嬰兒、為了一塊麵包賣身的女人、因沒火爐取暖而受苦的小孩,向社會不公下受苦的底下階層發聲。
當世人為巴黎聖母院失火同聲一哭,各國元首紛紛發文悼念,全球媒體爭相直播報道,當地首富LVMH集團主席阿爾諾(Bernard Arnault)和歐萊雅(L’Oreal)的貝當古家族更慷慨解囊助其重建,我們又有否為建築周遭,社會底層的群體發過聲,伸出過援手?尤其是法國民眾如《孤星淚》內的革命分子般,在馬克龍親商政府治下忍無可忍而起來反抗。連綿多月的黃背心示威,正警醒馬克龍及所有為政者,別忘了在文明社會中關顧底層弱勢的人文主義精神。
殖民主義:西方中心的視點和認識
巴黎聖母院失火令各國領袖和媒體關注的重視程度,也跟公眾對之前眾多古蹟在戰爭及騷亂中遭受破壞的關注程度相差得令人愕然。巴黎身為國際大都會,每年吸引全球數以千萬計的旅客來訪,聖母院得到如此重視也是無可厚非。不過在聖母院的尖塔倒塌的同時,眾多如敘利亞般身處戰亂的國家,其歷史遺跡正因戰火而摧毀,其中以有4,000年歷史的古城阿勒頗,其世界文化遺產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Aleppo)便損毀嚴重。這些古蹟在媒體上並沒得到如聖母院的萬千寵愛,更沒有首富巨企提出過要捐款修葺。
主流媒體以西方作為國際新聞的中心,與殖民主義的歷史不無關係。而巴黎協和廣場上的盧克索方尖碑(Luxor Obelisk)、羅浮宮內的眾多展藏,都是法國海外殖民擴張時所掠奪得來的,成為巴黎街頭和展館的裝飾品,令之贏得了美術之都的美譽。大陸憤青因對法軍火燒圓明園一事,而為對聖母院失火興高采烈固然不對,但我們在關注聖母院的同時,也應該對媒體西方中心的視覺有所意識,畢竟文化保育及歷史遺跡價值與維護應是超越國界的。而去年馬克龍提議將在非洲搶掠所得的藝術品歸還,令較落後的非洲國家得以發展其博物館事業,亦是在後殖民主義時代,前宗主國跟殖民地和解的文明之舉。
一場巴黎聖母院大火,讓我們反思文明發展過程當中,不同思想、不同階層、不同民族發生的碰衝和衝突。宗教與世俗主義的衝突,在200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釀成聖母院自身的災難;而今天的一場火災,也再令宗教與世俗主義的問題再度浮現。而聖母院下駝背敲鐘人的故事,也警醒我們雨果所宣揚的人文主義精神;在今天貧富愈見懸殊,社會愈見不公,各國民粹浪潮此起彼落,雨果的故事也當教為政者深思。聖母院火災所引起的全球關注,也反映出殖民主義遺留的西方中心視覺未完全糾正過來;在為聖母院惋惜同時,我們亦應關心世界各地遭戰火、天災破壞的寶貴文化遺產,也更應致力保護我們本土的歷史遺跡。
正如克格所說,佇立於塞納河畔的巴黎聖母院象徵了文明,而當中經歷過破壞、修葺、改建,以及日前的大火。就如一個文明一樣,也經歷過衝突、倒退、再生。但正如馬克龍和我們所期許的,人類文明將如日後重建後巴黎聖母院一樣,比以前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