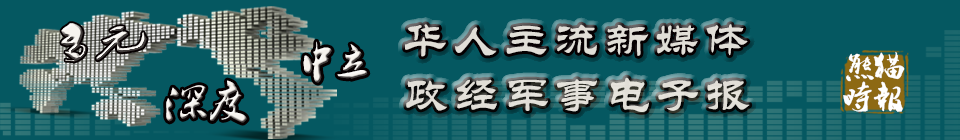【熊猫时报讯】75年前,美英两国如日中天。他们高举自由和民主的大旗打败了帝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诚然,他们的盟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这些美好的理想有着不同的想法,并在对德作战中出力最多,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战后秩序还是由美英主导。
1941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纽芬兰沿海的一艘战舰上起草的《大西洋宪章》规定了由英美主导的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最终击败轴心国后,他们设想的是一个国际合作频繁、多边机构协调和人民独立自由的世界。虽然丘吉尔拒绝将最后一点扩大到英国的殖民地,但罗斯福认为,英美关系太重要了,不能为此争吵太多。
几十年来,尽管多次鲁莽发动战争,冷战中歇斯底里,并抱着机会主义心态支持一些非常不民主的盟友,英美仍然保持着自由民主和国际主义的典范形象。
而如今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时代却打破了这种形象。在所有老牌民主国家中,正是英国和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取代了保守党派,统治了各自的国家。匈牙利和波兰同样如此,可它们从来都不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印度右翼也占了上风,但它也没有那样深厚的民主传统。
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借用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者的口号,高呼“美国优先”,后者比起支持罗斯福往往更同情希特勒。他们代表了罗斯福反对的一切。而英国背弃了欧洲,而丘吉尔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也是欧洲统一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尽管他对英国在统一欧洲中的作用含糊其辞)——绝不会宽恕这种做法。
怎么会这样?
原因当然很多,且不只在美国或英国出现: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制度的僵化、精英的自满、对移民的敌意等等。但我想说的是,这两个国家目前的麻烦与它们在1945年取得的最大胜利有关。
在摆脱孤立主义并打败轴心国之后,美国可能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有些飘飘然。将丘吉尔(他在美国总是比在英国更受欢迎)视为领导典范的诱惑,已经让许多美国总统误入歧途。他是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例外主义的牛头犬面孔,为自由而英勇站立,这对美国领导人的自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并不是第一个决定发动错误战争的丘吉尔崇拜者,以他在伊拉克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战争为例,萨达姆·侯赛因虽然残暴,但其威胁性远不如希特勒。
特朗普让“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死灰复燃,他对国际机构和美国在民主世界的盟友的厌恶,多多少少来源于布什的灾难性战争。特朗普吸引的是那种在美国海外冒险中被送去送死的人——白人、农村人、往往受教育程度低、对东西海岸精英深感不满的人。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布什一样是丘吉尔的崇拜者。他也对英美联盟有一种近乎救世主的看法,认为英美联盟的使命是要让世界摆脱当代的“希特勒”。在伊拉克战争时,他认为,在1940年英国最危急的时刻,只有这一个国家站在英国一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英国不得不和美国一起入侵伊拉克的原因。撇开历史错误不谈(美国还没有参加对德战争),布莱尔的怀旧情绪起到了愚蠢的作用。
但是,从1956年的苏伊士到1960年代的越南再到2003年的伊拉克,自1945年以来,怀旧并不是总统和首相们发动战争的唯一原因。另一个萦绕在白宫和唐宁街10号上的幽灵是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他在1938年对希特勒的“绥靖”。张伯伦意识到他的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或不愿意参战,于是让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远方的争吵”)。丘吉尔谴责这一政策是 “彻底而不可饶恕的失败”。战后领导人对被视为另一个张伯伦的恐惧,与重现丘吉尔辉煌的希望一样强烈。
虽然英国被这种虚妄的荣耀拖得接近破产,其最辉煌时刻的记忆却仍挥之不去,对国家的命运更具破坏性。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所有努力都保持冷漠,这不仅是因为克莱门特·阿特利( Clement Attlee)的社会主义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认为欧洲会摧毁英国的福利制度,还因为英国人无法想象他们的国家与其他欧洲强国平起平坐。英国已经赢得了战争;其他国家要么自己是纳粹,要么被纳粹占领。
即使在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这样的领导人意识到英国必须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与美国并肩作战的诱惑,特别是在遥远的战争中,也比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的愿望更强烈。当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时,其他欧洲人会很乐意让它发挥主导作用,塑造欧洲大陆的未来。美国对“特殊关系”的执念远不如英国,却一直吹着英国的耳旁风。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将拒绝抓住机会描述为英国“战后最大的错误”。
回到现在,孤立主义正风靡美国,英国日益与欧洲隔绝。他们最辉煌的时刻最终成了未来灾难的温床。
来源: PS
作者: Ian Buru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