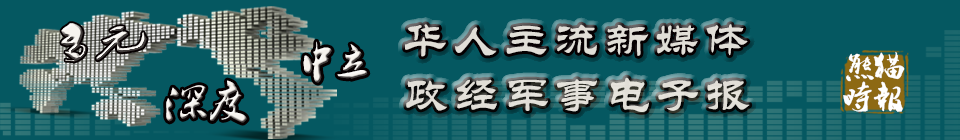尽管腾讯在汲取字节跳动的应对手法基础上既吸收又“创新”,但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开披露的信息,腾讯向美方提出的交涉包括:创建一个只为美国微信用户使用的美国版微信App;设立相关措施来保证美国版微信源代码的安全;将美国微信用户数据存储在由美国公司提供的“云”里面;美国版微信将由一家新设立的美国公司管理,其公司管理架构由美国政府批准认可;美国版微信的源代码交给独立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以防止可能存在的“后门”);对美国版微信进行定期的数据审计和数据传输的通报制度;建立严格的数据管理制度,限制公司人员随意访问用户信息。但美国政府以“不信任”作为回应。在政治强压下,腾讯尽管作了最大的让步,一度放低姿态,但WeChat在美的命运依然难以预料。
中国对美投资始终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中美建交的最初动力并非是经济利益的需要而是共同遏制苏联的威胁,这说明了中美两国都在奉行“现实主义”的态度,应对共同且紧迫的威胁。要维持中美的合作关系,经贸与投资当然是最稳妥的。相较于贸易,投资更需要建立良好的信任以及相应的规范和保障,否则冲突将成为常态。问题是,中美两国在预防投资冲突领域至今尚未建立共同的规范,这就意味着难以有共同的实践。在缺乏共有规范的现实下,两国往往以本国利益为中心,进行“应急”式处理,由于两国政府对对方资本依赖程度不同,这更加导致中国企业易于陷入被动,疲于奔命。
从时间轴来看,在2000年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长期处于爬坡阶段,由于投资体量偏少,甚至存在难以精确统计投资值的年份。2000年后,随着中国通过贸易等途径获取的外汇逐年增加以及中国政府逐步下放外汇的管制权,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增长。200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美国的产业和金融,美国众多的优质资产出现规模性的贬值,中国较好地抓住了历史性机遇,成功地开辟了对美直接投资的新纪元。这一阶段主要是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中国对美投资无论在金额、增长率、产业覆盖、战略资产投资成交上都表现突出。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联邦和州对外国资本的投资需求明显(比如奥巴马亲自推动设立了各州参与的“Select USA”项目)。奥巴马延续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升级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启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福耀玻璃在俄亥俄州的绿地投资、双汇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中航工业收购西锐等大型项目投资,但专司外资审查的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依然叫停了华为、西色国际、唐山曹妃甸、三一重工等批次的投资。在奥巴马时期,中国在美积累了众多的存量投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及辐射力,这链条中不仅包含中资跨国公司、政府、中间商、代理商、供货商、金融保险等系统性的关联体,同时由于商务的跨境拓展,投资牵扯了中美双方乃至多方的利益。
能够对美进行投资的企业往往是中国相关行业的领军型企业。从中国投资的类型看,大部分是商业性投资,即纯粹以获取投资利润为目的。在某些州受现有“购买本地货”规定的影响,本土美国生产的物品更受到美国民众的偏好,这样中国企业有动力在美国当地兴建组装生产线,这也是中企投资市场导向的逻辑所在。尽管早期寻求市场性投资以制造业和初级加工企业为主,但随后试图进军美国市场的中国服务型企业明显增加。这集中表现在如汽配、网信、游戏、医疗和地产上。此外,对美投资基本属于中资具体企业的战略性投资,其收购往往指向对公司谋划全球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产,于此提升企业的全球运营效率。
但不容忽视的是,安全因素依然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政府没有因为中国积极构建“相互依赖”而放弃实施对华中长期战略,即遏制潜在的“挑战国”。美国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就导致诸多的偏见和不对等。回顾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历程,尽管大部分的商业投资受到美国政府的“国民待遇”,但依然存在不少投资被“区别对待”甚至遭受“歧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体上经历了从国家主导到国家支持市场行为体自由投资的转变,在行业上经历了能源获取向战略资源以及高技术习得的转变。尽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额在金融危机后增长迅速,但中国在美国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以及科技型绿地投资上依然偏少,中国投资可以在具体选区上影响美国的社区就业,但很难说能对美国的产业结构及其发展走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此外,中国投资总体上偏向于低技术行业,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总体有利于美国。
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向高科技领域,而“预阻”高科技领域上中国在全球产业中的地位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环节。美国的智库如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企业研究所(AEI)等对中国的投资保持长期的跟踪分析。比如,亚洲协会早在2014年即公布了报告“High Tech: The Next Wave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merica”,其中就提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目标在于获取先进技术,并倡议美国政府注重中国投资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在这一逻辑下包括“中国制造2025”以及“网络强国”所涉及的先进算法、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机器神经网络、大数据等技术及其载体产业都在日后成为美国限制中国投资的方向。
2017年1月,奥巴马在离任之际曾特意委托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PCAST)发布了《确保美国在半导体领域长期领导地位》(Ensuring Long-Term U.S. 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s)报告。报告呼吁“加强国家安全控制,回应中国旨在破坏美国安全的工业政策”。报告指责中国政府通过设立15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基金资本对中企收购美国半导体的公司进行补助,提出美国政府有必要施压中国以增强其投资的透明度,收紧投资规则(tighten investment rules);对CFIUS进行改革,联合盟友对中国投资进行安全审查,形成新的各机构支持的外资安全审核环境,防止中国的工业政策破坏美国的安全,确保美国在半导体的全球领导地位。可以说美国政府内部早已对中美未来竞争和冲突的领域洞若观火。特朗普对中兴、华为的打击指向的正是芯片、光刻机等“半导体产业”,而对字节跳动以及腾讯的制裁则是力图削弱中国在具有比较优势的AI、数据处理领域的市场转化潜力。
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的安全认知和威胁认知决定了其对华安全战略的指向,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遏制竞争对手”。其实质在于维护自身主导地位、追求绝对安全和绝对优势,战略往往会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而不完全基于经济利益的算计。一旦制定好了安全战略,美国会依据强大的实力和完善的战略体系进行应对。结合美国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变化,笔者认为美国对待中国投资会采取以下政策:
其一,美国会鼓励非涉核心竞争技术的投资。中国对美的接投资有助于各州平衡财政赤字,提振就业和税收。一些非涉核心竞争技术类的投资,比如房地产、汽车配件、食品、海鲜、医疗、初级制成品等的投资往往有助于吸纳社会就业人口,推动社区建设。典型的例子如福耀玻璃的投资,由于不涉及敏感技术,其投资受到了所在州州长、州议会、联邦政府和参众议员的欢迎,而福耀的投资亦获得了代顿市政府、市议会的大力支持。像这类非关涉核心竞争技术但是能够充分解决就业的投资美国政府是持欢迎态度的。在特朗普执政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比如,2019年12月,中国家居企业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3313.SH)宣布以4645.6万美元(约合当前人民币 3.25亿元)购买 MOR Furniture For Less, Inc.不超过 85%的股份,交易就很快得到审批。
其二,美国会按照《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来审查增量投资。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中国投资的立法从严、从细,针对现有的法制漏洞进行修补和功能升级,并将权力更大程度地集中于CFIUS和总统,其立法主要针对中国。CFIUS在职能上更加具有权力,可以实施强制安全申报,这使得中国投资在合规上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FIRRMA明确将重点放在中国上,并特别指向了中国的“2025计划”。FIRRMA呼吁总统协助盟友及其他伙伴国家设立与CFIUS相似的审查制度,要求CFIUS建立与盟友和伙伴国家之间正式的信息情报共享流程;而投资人在其他国家的投资情况也将纳入到CFIUS审查的考虑范围。可以说,通过改革,任何违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对敏感行业的投资都将难以绕过CFIUS的审查,这进一步增强了法案的威慑力。美国政府会按照FIRRMA来审查中国的增量投资。
其三,中国对美存量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会成为美国审查监管的重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目前中国在美业已存在众多的投资项目,这种投资既包含了直接投资也涉及了金融债券等间接投资。早在2020年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即表示在新冠病毒疫情带来商业风险日益增大的情况下,要推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加强对在美上市中国公司审计工作的内部控制。SEC为审查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审计工作与中国政府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角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中,中国国有企业占比较大。中国国企在财务、会计、内控、账目合规上与美国的标准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新一轮的中美冲突。在直接投资领域,国有企业的投资往往集中在战略资产投资领域。比如,中航工业在美对航空产业的收购、中石化对美国东南部州石化以及页岩气项目的投资等。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国有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实现了历史上最好的业绩,尽管一些投资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美国监管部门尚未对这些投资实施强监管。特朗普上台后,FIRRMA进一步提升了外资审查的时效性,简化了流程,赋予了监管机构更大的权力,国有企业往往会被美国监管机构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目前,特朗普已经有计划地依据FIRRMA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或美国公民的敏感个人数据”领域的投资实施限制,展开针对微信和字节跳动在美投资的制裁和约束,正是这一法案的实践。按照这种趋势,国有企业将难以幸免。美国在对中国国有企业中兴的打击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开创了其“长臂制裁”的新模式,威慑了在美的国有企业。中国在美的国企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航空、钢铁、金融、和轨道交通等重要领域,在中美冲突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的严格审查将使得这些企业日益承受压力。
其四,涉及“军民两用技术”的投资会遭到美国的排斥。美国产业特征的一大特征在于国防与商业的深度融合,众多的跨国公司本质上是“军民两用品”的系统总成商(lead system integrator,LSI),美国本土的产业绩效往往代表的是“军民两用”型工业绩效。美国忌讳中国学习美国“军民两用技术”,但发展“军民两用产业”业已成为中国的国策,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制造2025”上,也表现在“网络强国”战略上。中国在AI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存在一定的竞争优势,而这些领域一样属于“军民两用技术”。美国针对腾讯的WeChat和字节跳动旗下TikTok的制裁背后的核心动力之一在于限制中国军民两用技术的市场运用,保障本土相应公司的寡头垄断地位。信息及其技术是“军民两用技术”的重要元素,这一点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惕。今年3月,特朗普发布行政令,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禁止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美国特拉华州公司StayNtouch的收购。该行政令要求中长石基于总统令发布120天(如经核准,可延长最多90天)之内完成对StayNtouch相关权益的全部剥离,且剥离期间交易双方应每周向CFIUS报告行动进度及剩余时间表。这种全过程的监视性手段背后是美国对华相应产业的深度不信任。
其五,司法诉讼将难以有效地维护中国投资的利益。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与总统权威,法院部门有时进行“回避”或者“踢皮球”。“三权分立”与“司法独立”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美国司法实行“辩论式”诉讼制度,这就要求双方都要拿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而针对“国家安全”的定义,CFIUS一直未予以明确的界定,这给安全审查带来了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但这可能导致CFIUS在法院审理上产生被动。美国法院是一种“被动”的应对机构,法官只对“可由法院裁决的争端”进行判决。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投资审查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系统性竞争的一个环节,也往往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实施的一个体现,因此法院往往会拒绝审理有“政治问题”的案件。最高级的联邦法院不会对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案件进行审理,往往会以“更适合由立法机关处理”的理由做出回避。美国司法中的“遵循先例”原则尽管实用,但是相对的,法官往往根据事实并考虑其他因素对涉及中企投资的诉讼做出裁决。历史上“三一重工”旗下罗尔斯建风电场案虽然由法院裁决中企获得诉讼胜利,但“三一重工”与美国政府最终选择相互体面的妥协。华为的诉讼则完全失败。
尽管9月27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做出了裁决暂缓美国政府关于将TikTok从美国商店下架的行政命令。但如果美国国务部门不服,依然可以在巡回上诉法院请求推翻特区法院的判决。而如果长期僵持不下,最终可能由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此外,美国内阁中的司法部对各级法院存在较为明显的影响渠道,这又增加了一个不确定因素。
其六,美国政府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总体政策已经转变,福利因素在下降,政府的安全偏好在上升。中国对美投资的份额以及影响由小到引起美国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主要原因有:其一,中国的经济体量逐年庞大,而中国奉行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国式“政商关系”导致跨国公司往往具有“非市场优势”,美国认为这是“不公平”的竞争;其二,美国政治精英担忧中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关系会通过跨国公司投资的技术习得进而转移回中国,或造成中国的贸易优势产生对美竞争优势;其三,美国担心中国跨国公司会将习得的技术转移至诸如朝鲜、伊朗等地缘政治对手,使其发展不对称优势,以此对美构成新的挑战。特朗普认为中国“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窃取”美国技术,从事“工业窃密”,政府“强令”在华美资企业以技术换市场,对在华美国企业实施“不公平”的竞争;中国在美的投资业已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国防安全;中国的直接投资有助于增强军事实力,习得美国的先进技术,进而挑战美国。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直接投资作为杠杆渗入美国的国内政治,进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福利因素的作用在下降,美国政府精英正在反思其过往对华的“接触战略”,并开始明确扭转以往的“接触+遏制”方式,提升“遏制”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实际上,美国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在应对中国投资议题上的决策地位得到了较大地提升,奉行的政策越发强硬。
当前中美投资领域的冲突反映了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中美结构性矛盾使得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难以脱离中美竞争这一宏观背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业已形成了一套明朗的规范和逻辑,即对国家利益、威胁、战略目标、可动员的战略资源以及对手的优劣势进行了理性且综合的评判,对如何使用战略资源实现国家利益目标有着精细的筹划。
总体来讲,美国政府所忧虑的是中国奉行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美国担忧中国式“政商关系”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并对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一直表达不满。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忧虑已阻碍多项交易的进行并导致一些交易走向“政治化”。中美经济上的角力焦点转移至对高科技领域的控制权和领导权的争夺。中国力图集中力量在一些重点领域实现突破和“弯道超车”,但无论中国研发出了多少核心技术,除了必备保留的军用技术外,其实大多数的技术需要转化为商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要转化为商业优势就必须有一定的跨国公司承载这些技术。为了实现商业利益,中国不能放弃美国这一全球大型市场,这逻辑犹如美国跨国公司不能失去中国市场一样。任何先进的技术如果失去对应的市场支持,其综合效能终究会打折。这也就意味着国家的技术发展难以实现相应的商业价值,并将削弱技术研发的总体意义。
中美竞争大环境已经在变,这一进程中“量变”与“质变”相互融合。中美合作要素在下降,竞争要素在上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中国投资政策始终奉行“积极防御”加“预防性打击或威慑”。如今,美国对华安全战略已经先验地设定中国为“竞争者”、“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建构为美国的“他者”。限于美国的实力以及制裁成本,特朗普力主“经济脱钩”,并借助疫情进一步推动“脱钩”。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对中国在技术和高科技服务性方面的投资进行了有力的“拒阻”。尽管中美经济的深度融合使得“脱钩”在短期内困难,但是美国政府逐一剥夺中国重量级跨国公司在美的投资却是把握了“要害”的“脱钩之举”。作为全球一、二大经济体的美中两国,在这一过程中消耗了太多的资源,付出巨量的“沉没成本”,尤其在疫情的当下,中美难以协作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这让众多的国家失望。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