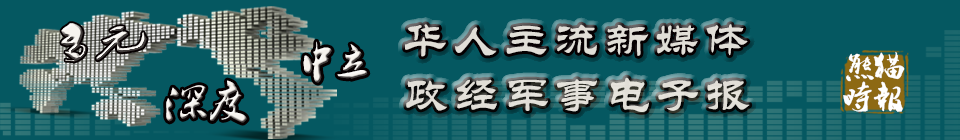【熊猫时报讯】这是前中国外交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外交学院原党委书记袁南生近日发表的『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中美关系的思考』,文章重点在讲中国的国际处境。在指出中美关系回不去了的大前提下,强调“中美关系需要 维稳”,指出要防止战略误判,尤其要防止对美国的误判,误以为美国已衰落,误以为全球抗疫战役已提出以他国取代美国来承担全球“领导责任这个历史性任务”。
原文:
2020年4月8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笔者认为,中央所说的“外部环境变化”,主要指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当代国际秩序的一个核心支柱。保持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中美关系的清醒认识,对于我们应对好新形势下的各种严重挑战,维护好中国的安全环境、发展环境,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极为重要。
一、中美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
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在2020年4月初的文章里预言,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国际秩序。此前,基辛格还曾表示,中美关系回不去了。他的见解有其道理。中美关系的走向与国际秩序的演变是连在一起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对国际秩序的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全球化一定程度上转向逆全球化;中美战略合作关系转向美国所谓的“中美战略竞争对手关系”;持续了数十年的中国战略机遇期转向一定程度的去中国化时期(逆全球化实质上就是去中国化);优势互补的国际大分工转为价值观认同的国际合作;随着美国不断退群,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很可能趋向于弱化、虚化,美国和盟友有可能另起炉灶,图谋将中国排除在外,以联合国为标志的雅尔塔“大国一致”模式的运转受到挑战。
中美关系与当年的苏美关系有很大不同,尤其体现在经贸关系上。当年,苏联和东欧国家组成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立足于经互会这个封闭的圈子;美英等国组成资本主义阵营,市场经济在关贸总协定体系中运行。今天,中美两国在 WTO 体系里创造了经贸往来的历史记录。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货物贸易增长了207倍,货物贸易总额达将近6000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则达1000多亿美元。中国经济在获得巨大的出口、就业、技术、人才等方面利益的同时,中国也成为美国成长最快的海外市场:美国向中国出口销售26%的波音飞机、56% 的大豆、16%的汽车、23%的农产品和23%的集成电路。中国是美国飞机、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农产品、汽车和集成电路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处于逆差地位,中国人在旅游和教育消费方面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收益。2016年,中国在美国的非金融类投资为500亿美元,中国投资遍布美国44个州,为美国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与美俄关系相比,中美之间的经贸利害关系要远远高于美俄之间的经贸利害关系。比如,中美有将近60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而美俄的贸易额只有150亿美元,且两国在能源等领域存在竞争关系。俄罗斯经济规模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俄罗斯GDP目前只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GDP。经贸份量不足是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敢于对俄罗斯进行集体制裁的最重要原因。
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中美关系有很大不同。中美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敌手阶段、对手阶段、联手阶段,现又回到对手阶段。敌手阶段指的是局部热战时期——朝鲜战争时期;对手阶段是指冷战时期中美建交之前这一段,这一时期,美国采取对华遏制政策;联手阶段是指中美建交以后到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之前这段时期,特别是“9·11”事件促成了中美联手,在此阶段,接触成为美国对华的一项长期政策;现在,中美关系又回到了对手阶段。这两个对手阶段并不是一码事,虽然中美在两个阶段都是对手关系,但在前一个阶段,美国仅将中国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对手,谈不上战略竞争;在后一个阶段,即现在这个阶段的对手关系,按美国的说法,是“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关系。特朗普和其他美国政要把中国看成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意思是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想要修正既存的国际秩序。美国的应对办法是以“全政府”的方式(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简称WGA)同中国进行长期的、全方位的战略竞争。
新冠病毒流行前和流行后的中美关系会有很大不同。一是民意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外一些民调机构的数据表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民间,对对方持负面看法的人数都明显上升,均已占多数。美国民众总体上对华友好度持续走低,已降至本世纪最低,是中美建交四十余年以来的“历史最低”之一。二是经济贸易关系有很大变化。尽管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正式签署后,两国的贸易战告一段落,但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美国并未取消第一阶段协议签订之前对中国加征的诸多关税。新冠病毒流行后,美国资本有可能加速撤离中国市场,中美之间缺乏进一步相互投资的意愿。三是其他方面的合作动能明显衰减, 中国人到美国旅游、留学、表演、办展、移民等热度都会趋于回落。四是中美两国战略互信远不如以前,其趋势难以逆转,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变化。未来,美国在贸易关系、技术竞争、网络安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涉藏涉疆问题上,还会加大向中国施压的力度。
有人说,这次疫情将加速去全球化的趋势,“新冷战”将加速美国与中国的“脱钩”。这是否可能?疫情过后,美国对华政策有可能变为以遏制(containment)为主,走向“新冷战”、中美“脱钩”的可能性虽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仍有待观察,不可掉以轻心。
所谓“新冷战”,就是中美“脱钩”,包括科技脱钩、投资脱钩、产业脱钩、教育脱钩、人才脱钩,等等。美国也确实在做一些推动“脱钩”的事,但中美之间真会“脱钩”吗?本人认为不可能。2013年,笔者出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在任期间,平均每7分钟便有一架航班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每天往返于两国之间的旅客达1万人以上,一年下来约400万人。中国旅客在美平均消费达6000美元。中美两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加州旧金山市有四分之一的公民是华人,居住在旧金山领区内的清华大学毕业生达1.2万多人,北京大学毕业生达7000多人。中美真正“脱钩”并非易事,但中美之间的联系、往来、互动,其频率十之八九不会像以前那么频繁了。但是只要经贸往来脱不了钩,中美就不可能彻底“脱钩”。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太大,中美相互联结的产业链、供应链太过紧密,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资金需求,中美在高技术领域相互依赖太深,中美两国人民往来太紧密,中美宏观经济协调对全球市场影响太大——换言之,中美若“脱钩”,必将引发国际秩序的极大混乱。况且,真正的“脱钩”必将涉及方方面面,其过程必然错综复杂、劳神费力,甚至伤筋动骨。
在席卷全球的严重疫情中,美国没有释放出足够的团结合作的信号,也完全没有体现出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意愿和能力,自己应对不力、陷入困境,又试图将责任推诿于中国。美国政府的行为进退失据,其现状和作为对中国不利是肯定的。美国成为全球疫情中心大国,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和死者数都高居世界第一,特朗普由此卷入争议风暴,备受内外指责。新一轮美国大选将至,非理性的言论很多,而“中国问题”也被裹挟于其中,特朗普面临选情走低的危险,谋求连任的努力有可能付之东流。特朗普拿中国应对疫情初期的困难说事,以转移美国国内注意力,希望以此稳住选情,由此中美两国的舆论环境受到毒化。
疫情过后,全球化进程不会中断,但可能出现另一种走向。旧的全球化道路强调成本优势,实现国际分工;未来的全球化则很可能强调政治价值的趋同,中国可能遭到来自政治价值不同的国家的排挤打压。但是,离开了中国的全球化,不能被称为真正的全球化;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会有完整的世界市场,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和世界市场,完全可以扬长避短,维护并拓展自己的利益边疆。
二、中美关系需要维稳
2017年4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会晤中,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中美关系正常化45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得到了历史性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实际利益。中美关系今后45年如何发展?需要我们深思,也需要两国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在新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2019年6月29日上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举行会晤。习近平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益。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歧,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稳住中美关系,有利于稳住国际秩序。中美关系的稳定程度同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同国际秩序的稳定程度成正比。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毛泽东、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来看,他们都非常重视、亲手谋划中美关系。毛泽东从“一边倒”的反美外交,发展为“一条线”的联美外交,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改变了世界格局和走向。邓小平自“文化大革命”中复出不久,就成为周恩来总理处理外交事务,尤其是同美建交问题的主要助手。他在困难局面中接手中美关系大棋局,纵横捭阖,推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最重要的外部环境。稳住中美关系,符合毛泽东、邓小平的遗愿。
从地缘政治的维度来看,中、美、俄三国组成了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三角关系,美俄长期争霸,中国作为杠杆,处在左右逢源的、有利的战略地位。如果中美“脱钩”,则意味着中俄角色将随之发生易位,中国成为美国围堵、牵制的主要对象,俄罗斯则成为杠杆,左右逢源,坐收渔人之利。中美“脱钩”,意味着中国事实上扛旗、出头,由此造成中国外交主动权和自由度的减少,意味着中国外交成本的增加和外交收益的递减。有观点认为,中俄可联手与美国抗衡,这种想法并不可取。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中美如果真的“脱钩”,中美、中俄、俄美三对双边关系的走向会出现何种变数,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所在,都是值得慎重思考的问题。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目标来看,如果中美“脱钩”,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尚不能实现合作共赢,谈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何稳住中美关系?一是要保持战略清醒,认清我们仍然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二是保持战略耐心,防止急于求成;三是守住战略底线,既韬光养晦,更奋发有为;四是防止战略误判。尤其是要防止对美国的误判,误认为美国已衰落,误认为美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显露出的种种问题已说明美国“霸权式微”,误认为全球抗疫战役已提出以他国取代美国来承担全球“领导责任”这个历史性的任务,误认为中国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最先受到冲击、最早走出疫情,是给中国带来了与美国竞争霸权的历史性机遇——如果这样从竞争霸权的视角来审读中国作为,那显然是完全错误的。要看到尽管近年来美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但美国同自身相比仍在发展,并没有走向衰落。过去100年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始终保持在四分之一左右,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可能是这样,美国继续拥有科技霸权、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仍然是世界第一地缘优势大国、农业大国、教育大国、科技大国和资源大国。以农业为例,美国以不到300万农业人口,成为世界粮食生产出口第一大国,粮食出口占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一半,而中国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美国经济总量已超过20万亿美元。横向比较,只有中国、印度、越南、埃塞俄比亚等少数国家长期经济增速超过美国。美国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下降,主要是中国和新兴大国力量的上升,相对来说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下降了。还有美国的单边主义、“美国至上”,也造成了美国“软实力”的下降。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因此自然迎来重大机遇。中美任何一国的经济困难都会给对方、给世界带来消极影响。由于美国拥有最顶尖的科技、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和全球流通货币,美国很可能率先走出经济困境,回归正常轨道。
当然,稳住中美关系,并非一厢情愿之事,需中美双方相向而行。中国必须全面评估中美关系,在不分道扬镳的同时,也要做好多手准备。
三、坚持韬光养晦,奋发有为
诚然,中国的抗疫成绩不俗,但预言新冠疫情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这种观点显然属于战略误判。中国国内部分有识之士担忧,这次疫情将助长国内的民族主义,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他是在迎合美国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在搞单边主义。对中国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如不加以防范,任其发展蔓延,国际社会很可能会因此而误认为中国也在追求“中国优先”。
近几年来,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国际上合流并扩散开来,特朗普通过呼吁“美国优先”等口号当选美国总统,就是民粹主义思潮的产物。中国国内也常常感觉到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涌动,有人早先把这方面的言行名之为“愤青”,现在亦有人称之为“战狼文化”。中国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不奇怪,其存在与发展,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源流和现实基础。
一是受“华夏中心论”即“天下观”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主导对外关系的核心思想一直是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这种思想来源于华夏民族的自我优越感,认为中国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处于世界的中心,称之为“华夏”,西方的入侵对固有的“华夏中心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军事上的失败使得中国被迫卷入了近代世界体系,传统的华夷秩序和天朝观念逐渐崩溃,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华夏中心论”随之逐渐衰落,而民族主义思想则渐渐兴起,作为一种新的精神纽带逐步取代了“华夏中心论”的作用。
二是受“必诛论”的影响。“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对外交往中听到不同意见,有人动辄拍案而起,某些情况下,“对话”变成了“对骂”,甚至变成了 “独骂”。
三是受“必胜论”的影响。既然中国体制优于西方体制,美国已经衰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中国取代美国的老大地位就是必由之路、指日可待的事。
四是受“必战论”的影响。“中美必有一战”“中日必有一战”“中印必有一战” “中韩必有一战”“中菲(律宾)必有一战”“中越必有一战”,等等,这些年来,诸如此类的声音不绝于耳,总有人把轻言战争与爱国简单地画上等号。
民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成功的外交往往能善于驾驭民意,使民意成为对外交往中的一张牌,但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因为打着“爱国”的旗号,容易挑动民意、煽动民意和裹挟民意,在这种情况下,民意又容易绑架外交。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与人打交道要“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战狼精神”却同中国传统文化背道而驰,如果裹挟了民意,则后果堪忧。外交被民意绑架度与外交空间成反比,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声音越大,受此影响,对外交往中对抗就更容易代替对话,中国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少。
避免盲目的民族主义,一是要普及知识,重申常识,防止信息不对称,让民众了解更多历史。部分民众滋生盲目的民族主义,同信息不对称、“坐井观天”分不开。例如,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值得自豪,但有人由此飘飘然、骄傲自大,到处高调宣扬“厉害了,我的国!”,这就可能出现问题。其实,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GDP就已名列世界第二。到1927年,正是中国军阀混战,国力衰微最甚之时,《生活》周刊前主编邹韬奋于同年10月的《生活》周刊上引述了一篇重要资料,指出“中国的国富居然列在全世界第三位,在德、日、法之上”。1949年,中国GDP下降至第四位。按照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计算,公元元年中国GDP总量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的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公元1500 年(即中国明代时期)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几千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有资格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先后三次名列第二,一次是明代以前,一次是近代史上被英国赶超,一次是现在这个时期。了解这些情况,有助于保持清醒的头脑。二是要加强引导,改进思想方法,防止看问题简单化、标签化、情绪化,例如简单地把砸日本车等同于爱国。三是要守住底线,例如,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 美国成为新冠病毒世界第一疫情大国、死亡逾十万人,绝非值得兴奋、恭喜之事。
民众关注外交问题是好事,外交问题交由专业人士处理与民众关注外交问题不矛盾。民众信息越对称、越成熟,越理性,外交空间就越大。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外交人士面对公众的声音,一要了解民意,尊重民意,这既是由“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的宗旨所决定的,也是世界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二要不唯民意。无数事实证明,外交被民意所绑架,难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加拉罕(Lev M. Karakhan)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无条件放弃依据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夺的领土。联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使华,谈判与中国建交,希望以此对冲来自英国对苏俄的巨大压力。时任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对越飞说,如果苏俄从外蒙古撤军,中俄可立即建交。但北京大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无条件与苏俄建交,并宣称如顾不答应,就像五四运动对待参与巴黎和会谈判的曹汝霖等一样,一把火烧了顾家。顾说,你烧了我家,我也不答应,哪有占着中国大片领土,又要建交的道理。后来顾维钧家收到一个包裹,打开时真爆炸了。尽管这样,顾维钧仍不让步。民间看不到加拉罕对华宣言只是一个外交姿态,并没有打算真正实行,历史上也确实没有实行。后来,越飞到上海,与在上海的孙中山发表《孙越宣言》,苏俄承诺帮助中国国民党,孙表示俄不必从外蒙古撤军,由此埋下外蒙古脱离中国的种子。历史证明,顾维钧是对的。民众毕竟不是外交专业人士,一味迁就民意,甚至讨好民意,很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最终也会损害民众利益。
稳住中美关系,必须坚持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并没有过时。只要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韬光养晦不等于不强硬。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本身就包含该强硬时应该强硬之意。“韬光养晦”是一把插进刀鞘的宝剑,外交上的“韬光养晦”是指用谦逊的姿态与他国交往,而不是咄咄逼人,强人所难。有人认为韬光养晦就是“缺钙”、软弱,这完全是误解。跟人打交道,把刀拿在手上,人家是什么感觉?“亮剑” 是军人的职责所在,处理外交事务则应韬光养晦,把宝剑插进刀鞘,不亮剑,人亦知有剑。顾维钧在外交场合,对任何人都称“您”,因为打外交仗,不在于嗓门大,不在于是否亮剑,而在于是否在理。南宋使节王伦四次出使金国,在谈判桌上拿回的土地,比包括岳飞在内的任何一位抗金名将都要多,他靠的是智辩,而不是对骂。就韬光养晦问题,社会上有争论是正常现象,是好事。中国外交应该“强起来”,而不是单纯地“强硬起来”,因为外交强国应做到该放下身段的时候放得适度,该求人的时候求得恰当,该说硬话的时候硬得上去,该出手的时候出得精彩。
来源: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作者: 袁南生–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外交学院原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