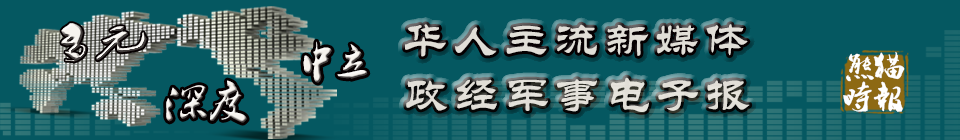阿根廷政治宛如一個鐘擺,在左右間激烈晃動,且頻率越發加速。兩年前左翼貝隆主義者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擊敗新自由主義者當選總統時,他高喊「我們回來了」的場景仍歷歷在目,但日前就在國會選舉遭遇重挫,使得貝隆主義者近四十年來首失參院多數,執政黨也就此在立法方面淪為跛腳鴨。雖說這等結果是民眾對政府無能的控訴,但由此帶來的潛在政策搖擺卻也進一步加深了困境。在沉重外債和通脹危機之下,阿根廷還能找到出路嗎?
自阿根廷1983年擺脫軍政府以來,先經歷了20年新自由主義的洗滌(大體先後為右翼保守及右翼貝隆主義),又迎來12年左翼貝隆主義回潮,再有4年右翼主政,接着便是兩年前費爾南德斯的當選。但他任期不過一半,右翼就迅速殺個回馬槍。
根據11月14日的國會中期選舉結果,執政聯盟在眾院選舉中整體得票率落後右翼聯盟8個百分點,在改選的半數席位中比對方少上11席,最後僅以兩席微弱優勢維持了第一大黨局面。參院改選結果更具決定性,貝隆主義者整體得票率落後了近20個百分點,是1983年重回民主以來首次失去參院多數席,此後立法需仰仗右翼合作。
地獄開局與疫情重創
這等結果並不讓人意外。費爾南德斯本就從前任馬克里(Mauricio Macri)那兒繼承了一個爛攤子:逾40%的年通脹率、狂瀉不已的匯率(馬克里四年任內披索貶值80%),以及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新借的440億美元外債(2022年和2023年就要陸續償還)。如此糟糕的開局,再加上新冠疫情這等天災擾亂全球市場,身家性命取決於大宗商品出口行情的阿根廷便首當其衝,財務危機進一步加劇,並在2020年4月成為疫中首個債務違約的國家,這也是該國的第九次違約。
此後發展便是循貝隆主義者的慣性,由於其強調政府干預和福利舉措,與IMF倡導的自由開放市場以及財政緊縮原則背道而馳,且其民族情緒通常將同意IMF條件視為向外國勢力屈服,雙方談判之路相當艱難。阿根廷政府儘管去年與私人債券者成功重組了660億美元債務,但與IMF的440億美元債務卻是至今仍未談妥,如此僵局不僅在疫情期間掐斷了該國獲取更多貸款的源頭,更可能在明年3月首個主要還款日時出現再度主權違約的危機。
與此同時,費爾南德斯還需履行貝隆主義者對勞苦大眾的福利義務,外債不夠只能印鈔來湊,但此舉無異於飲鴆止渴,年通脹率進一步提升至逾50%。而杯水車薪的福利措施也抵禦不了他實行的拉美地區最漫長封鎖,過去兩年已有400萬民眾返貧,且新冠病歿人數也高達11萬人,按人口規模調整後與無為而治的鄰國巴西相近,就更是引發民眾憤怒。儘管費爾南德斯為挽救民心,上月緊急凍結了逾千類商品價格,但看不到希望的選民還是拿選票懲罰了執政黨。
可悲的是,民眾雖然抒發了怒氣,但國會跛腳鴨的命運只會致使執政黨更加舉步維艱,更難以帶領阿根廷擺脫困境。同時,這也抬高右翼兩年後重回玫瑰宮主政的可能性,帶來新一輪政策轉向,不過以史為鑒,如此迅速搖擺往往只會進一步加深困境。有強制投票規定的阿根廷無論如何投票,也難以投出一個光明的未來。
左右路線都難以解決的困局
歸根結底,阿根廷所面臨的困局並不是單純的左翼或右翼路線能夠解決的,該國脆弱程度宛如瓷人走鋼索,一不小心就會摔得粉身碎骨,而左右路線主政者每一次大開大合的政策轉向,就使鋼索搖晃得更加厲害。同時,國際大環境隨時可能吹來一陣逆風,無論何等路線的瓷人也無法避免被吹落的命運。
從國內經濟結構來看,阿根廷最突出的問題是過度依賴農業出口,2019年農產品出口價值佔整體出口貨物價值57%。這是該國幾百年來對於潘帕斯草原這一農牧業寶地的路徑依賴,以及上個世紀失败的「進口替代工業」的產物。雖然阿根廷曾清晰意識到發展工業的必要,四五十年代執政的貝隆(Juan Perón)還曾擬定了以工業為主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但他的全盤國有化計劃、普及工會、福利民粹政策以及反對外資流入扼殺了市場活力。隨後長達三十年的軍人反復干政以及血腥鎮壓貝隆主義者引發的亂局,也使該國錯過了一段黃金發展期。
等到文人八十年代重新掌權後,調整經濟結構的優先級又讓位於又因兩次大型債務危機——第一次是因軍政府70年代過度借貸石油美元,後因1979年石油危機爆發而崩潰,第二次是因九十年代末右翼貝隆主義政府過度向IMF借款,又遇亞洲金融風暴,該國經濟局勢直到2003年才穩定下來。但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崛起的背景下,阿根廷此時發展工業既不具備比較優勢又缺乏外國投資者問津,只能被束縛於農業大國的位置。
與此同時,貝隆主義的幽靈持續徘徊在這片大地,並因軍政府鎮壓而獲得無上光環。此後執政的貝隆主義者也方便地利用福利民粹主義吸引選票,但這往往帶來過高的財政負擔且帶有「授人以魚」的短視特點,例如2007年至2015年掌權的克里斯蒂娜(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政府,其對窮人的直接現金轉移項目雖然減少了三成的極端貧困,但過度印鈔帶來的通貨膨脹卻吞噬了廣大中產階級,且為此後繼承者埋下了公共開支居高不下的禍根,使其缺乏財政空間改革。
在無力調整經濟結構、福利民粹之風限制財政政策空間的情況下,該國猶如洶湧國際環境中的一葉扁舟,難以抵禦隨時刮起的逆風。無論是2008年金融危機、2014年大宗商品繁榮期結束、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及2020年疫情,都對該國帶來巨大衝擊,引發經常項目收入和財政收入急減。在此等情況下,無論是何派政府都難以抵抗選擇印鈔的捷徑,彌補財政窟窿之際,引發貨幣貶值提高出口優勢,但也被淹沒在進口工業品和消費品騰貴帶來的通貨膨脹之中。
更糟糕的是,每每在這等經濟下行周期,巨額外債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便搖搖欲墜,因為敏銳的投資者見勢不妙就紛紛撤資,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對此,左翼政府通常採取資本管制,但如此限制性的環境從一開始就讓投資者望而卻步,右翼政府雖是開放市場,卻又在逆風時刻更加脆弱。比如馬克里政府雖以自由開放原則換得IMF歷史性高額援助,本打算為阿根廷經濟打上一劑強心針,但2018年因中美貿易戰的大環境逆風,以及美聯儲加息倒吸美元資本回流美國,便引得國際投資者紛紛撤走,引發披索狂貶,馬克里動用三成IMF借款救市仍無濟於事,他提振阿根廷之夢就此破碎,只加深了沉重的債務負擔。
由此可見,單純的左翼和右翼路線都很難解決阿根廷的困境,且激烈的左右路線轉換只會讓投資者和民眾更具有不確定性,傾向於短期投機倒把,執政者也往往只會趁短期在位時期大撈一筆,或以短視福利政策籠絡人心。只有去政治化的理性政策設計,長期穩固的國內政治氛圍,且在有益國際市場的加持之下,阿根廷才能有可能獲得一絲生機,跳出不斷循環的危機。不過,這又談何容易?

阿根廷民眾今年9月上街遊行反對費爾南德斯政府。(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