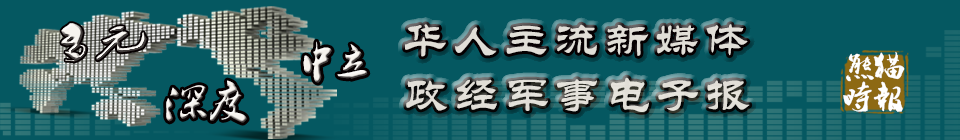1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歐美五國行來到英國的第三站,他與英國首相辛偉誠(Rishi Sunak)簽下了全文長27頁的《日英相互准入協議》,確立了雙方在對方領土部署武裝部隊的各種細節,使英國成為日本繼澳洲之後第二個談成相互准入協議(RAA)的國家,以及首個與日本達成RAA的歐洲國家。跟岸田此前到訪法國和意大利、此後到訪加拿大(13日還會到美國)大家「談」安全合作不同,「日英RAA」是一份有實際意義的文件,岸田與辛偉誠簽字後,協議更需要兩國國會通過作實。
辛偉誠在簽字之時間接提到1902年《日英同盟》共抗沙俄的過去,今時今日的日英RAA也確有這個百年前同盟的影子。根據日本外務省的官方通稿,這次日英軍事合作的「背景」是兩種對於既有國際秩序的挑戰:其一是「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進侵」,其二則是「在東海和南中國海以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嘗試」——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這個嘗試的主角就是中國。
這個協議其實已非日英軍事關係愈行愈近的第一個訊號。此前在2021年9月,英國新航母伊利沙伯女王號(HMS Queen Elizabeth)首次出航就來到印太地區訪問日本,並與日本自衛隊進行其首次演練。其後,兩艘英國巡邏艦已長駐橫須賀美國海軍基地。
當然,跟百多年前的世局不同,今天「後-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主要玩家是中國和美國。就算是2022年入侵烏克蘭引發軒然大波的俄羅斯,其行動的重要背景因素也離不開中美的消長和競爭——試問如果中國仍然只是個羸弱的人口大國,不得不順應西方的「國際規序」,又或者美國沒有「印太轉向」而依然以冷戰時代的大西洋主義為外交主軸,普京會否如此輕率向烏克蘭動刀?
「圍堵中國」的機遇
雖然中方否定「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必然性,但此刻美國對於中國已明顯採取了一種「圍堵政策」。特朗普時代發動的貿易戰和主要針對華為的科技打壓,從其只要求中國多買一些美國貨的2020年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看來,背後並無深遠的戰略考慮。但此等莽動卻確立了美國壓制中國崛起的兩黨共識:從華府建制代表拜登(Joe Biden),到原本經營健身室、後來靠QAnon陰謀論打響名堂的共和黨極右眾議員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抗中」意圖如一。
拜登當局的這種「圍堵政策」在其10月公布的對華晶片禁令中表露無遺,該法令對中國企業作出一刀切的半導體出口限制,更禁止美國公民為中國半導體發展服務,明白不過地撕破了某中國企業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往日藉口。
「圍堵政策」的另一面,則是拜登強調的盟友外交。在半導體產業上,美國正積極拉攏荷蘭、日本,甚至韓國,加入美國主導的對華包圍網。在軍事上,美國則鼓勵盟友加大軍事投入,去為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服務。
這一種新時代下的地緣政治發展,引伸出大國爭霸的形勢,重燃起不少有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的國家企圖再次參與改變歷史的「大國夢」。
「全球英國」與「日不落」
在英國,脫離歐盟的背景,其實就是英國能夠在全球茫茫大海上單打獨鬥的想像,認為歐盟的種種規範對英國而言只是綁手綁腳。脫歐公投後上台的留歐派文翠珊(Theresa May)為迎合脫歐派而提出的「全球英國」(Global Britain),其實就極有「日不落帝國」的影子。這種歷史想像固然是脫離現實的——歐洲人對於英國脫歐的一大批評就是「歐洲有兩種國家:小國和不知道自己是小國的小國」——但想像當然不必符合現實。
此刻的「英日RAA」,可算是軍事維度中「全球英國」乘着中美、中日競爭之時勢的實踐。正如伊利沙伯二世女王號首航即到印太的決定一般,這個與日本的軍事協議也是在「脫歐大將」前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任內開始商談的。英國脫歐、全球英國與英國印太政策的關連不言而喻。此刻的印裔首相辛偉誠,雖然沒有約翰遜的英格蘭本位氣息,卻也是根正苗紅的脫歐支持者。(有趣的是,不只辛偉誠,其實連約翰遜本人也是土耳其移民的後裔。)
但在這個「全球英國」的想像之中,心懷「大國夢」的英國人卻不得不接受一種矛盾:日不落帝國是國際政治的主角,但全球英國只能是美國地緣政治佈局的棋子。
日本的「中國威脅論」
另一個有着「大國夢」想像的當然是日本。自二戰軍國主義失敗之後,日本一直有一小撮右翼分子心有不甘,至今經過公關上的溫和化後,就變成了修改和平憲法的力量。日本的「大國夢」並不像英國般「日不落」,卻至少是要保持在東亞的大國地位。然而,殘酷的現實卻是,從人口和人口構成的發展來看,日本根本不可能是東亞的大國,在其經濟規模早就被中國超越和拋離之後,日本更愈來愈被人與「前殖民地」韓國相提並論。
中國威脅論,就成為了日本右翼針對中國崛起、試圖扭轉歷史走向的解方。一方面,日本要阻止中國國勢在東亞獨大,必需借力美國,鼓吹中國威脅就是日本能從中美競爭中達成自身地緣政治目標的利器。近年美國用以在亞洲凝聚抗中陣線的「自由開放印太」理念,甚至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重生,背後其實也完全來自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而另一方面,鼓吹威脅,也能壓服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傾向,使民眾更為支持日本擴軍甚至修改和平憲法——畢竟這些只是對於「威脅」的「被動回應」而已。
大國想像終受現實局限
在中美競爭的新時代之下,「大國夢」其實不限於英日。例如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治下的法國,就一直希望在世界走向中美權力兩極之時,掙脫二戰和冷戰遺留、由美國主導的大西洋格局,再以「歐洲」為中心,建立起世界另一個權力重心。
法國一向是北約和美歐同盟之中不太心甘情願的成員——畢竟法國今天尚是歐洲唯一擁有遍布美洲、非洲、亞洲剩餘殖民主義幅射能力的國家,而在地理上其實只是亞洲延伸出來的一角、根本算不上是「洲」的歐洲,當然也是帝國主義歷史中夜郎自大的產物。再以歐洲為權力中心背後的歷史性情意結實在是明顯不過。
值得留意的是,法國近年也加強了與日本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合作。這次岸田訪法與馬克龍見面期間,印太安全就是主題,而雙方也決定了會在本年上半年再舉行兩國外長、防長的「2+2」模式會面。近年在西非借反恐為歐洲軍力小試牛刀失敗後,法國在印太的未來行動絕對值得留意。
另一個還有「大國夢」想像的當然就是俄羅斯。若非普京有基輔羅斯(Kievan Rus)唯一繼承國的歷史理解,又或者白羅斯、烏克蘭、俄羅斯三國本來是血濃於水一家親的想像,去年2月的俄烏戰爭根本就無從談起,即使俄羅斯東有中國盟友支撐、西有美國印太轉向的客觀條件支持亦是如此。
正如普京在烏克蘭戰場上所經歷到的一樣,人們的政治想像往往會受到現實所局限。國際政治作為一種社會建構,並沒有客觀的現實,卻是客觀的現實與人們的想像之間的存在。畢竟,用來描述新興強國威脅到現有強國國際霸主地位時的戰爭傾向的「修昔底德陷阱」也不是一種自然律法。可是,如果人們的想像與客觀的現實太過格格不入,最終憑想像而行事的人只能跪倒於冷酷的現實之前。這也是出於各種不同原因而各有不切實際「大國際」的為政者應該銘記在心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