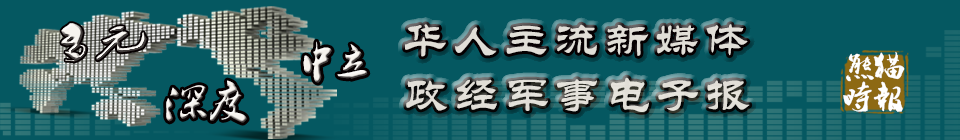【熊猫时报讯】正如雅典旅游局很少提到的,他们的美丽城市不仅是民主(democracy)的摇篮,也是民主的陵墓。古人以字面含义来定义“民治”(这种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延续下来):举行群众集会,一个议题接一个议题,面对面地直接投票。美国的国父们回避了这个字母“D”开头的词语(美国宪法里并不包含这个词),那是因为当时这个词仍然采用古希腊的那种定义。时至今日,美利坚合众国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采用的间接投票制度与古希腊民主之间的差异,就像现代建筑与多立克柱式(Doric order)的差异一样大。
民主有程度之分,少一点可能胜于多一点:西方基于这些原则而崛起。为了生存,西方可能不得不再次留意这些原则。
没有哪种全球趋势比民主危机得到了更好的记录。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是一个案例研究,这位总统表示,在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他可能不会承认败选。从剑桥大学(Cambridge)的多位学者筛选出的大量数据来看,特朗普并没有那么独特。世界各地公众对民主的疑虑越来越多。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民主不满意。这类话题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令人欢呼的书名包括《通往不自由之路》(The Road to Unfreedom)和《民主的终结》(How Democracy Ends)。
关于威权未来的构想貌似合理。但有时候这些构想读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在我们所知的民主和邪恶的对立面之间,似乎不存在任何制度。一方的危机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突破。
这种令人窒息的二元论不允许中间路线。它不允许少一点的民主。和以前一样,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远一点,既可以提高前者的质量,又能够让后者最终掌权。
计算一下有多少方法吧。两次选举之间较长的时间间隔将激励有远见的治理,并减少选民之间争吵的频率。给予技术官僚更多的权力将尽可能地使政策领域去政治化。如果这种情绪透着一股傲慢,请记住,央行发挥着巨大的分配影响,让一些公民比其他人富裕。尽管如此,在整个富裕世界,呼吁货币政策民主化的呼声并没有震耳欲聋。允许技术官僚插手一个或两个其他的杠杆并不会突然开创先例。
至于对直接民主的限制,如果有这些限制,英国公共生活现在就不会那么败坏了。美国并不热衷于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公民投票,但公民投票导致了美国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州的治理不当,这是一个本不应该败坏的地方。
在一本关于新冠疫情的新书《警钟》(The Wake Up Call)中,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分析了抗疫最成功的国家以寻找线索。他们总结道,起作用的不是大政府,而是能力和信任。他们的专著可能会在未来避免大量无目的政府支出。然而,两位作者回避了一点:其中许多政府的运作与它们国家的选民是有一定距离的。实行“指导式民主”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也有一些更为微妙的例子。除了短暂的中断,日本实行一党统治。台湾在其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实行类似的模式。就连德国也对全民公决设置了宪法限制,自1982年以来,德国只有过三任总理。
任何朝着这个方向的改革都将被民粹主义者视为对自命不凡者的纵容。但是民主程度和民众幸福程度之间没有线性关系。近年来导致反政治的原因显然是人民力量的不足。美国最不被信任的大机构是国会,其任期两年的下议院与其说是一个立法机构,还不如说是各种竞选总部的集合地。不经过选举产生的美国最高法院赢得的信任比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还要多,而与大多数公民没有联系的美国军方又比前两者赢得了更多的信任。
在英国更是如此。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担任首相期间,选民激他做成英国退欧,卡梅伦在五年内举行了三次大规模公投。加上英国上议院的改革和权力下放,英国退出欧盟前的几十年是英国现代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在所有这些被迫与选民亲密接触之后,国家招致了选民的蔑视,而不是信任。由此可见,退一步并不一定会引发一场革命。最终,公众对民主的愤怒是一种隐含的自我批评。
一步有多远?经济学家加雷特•琼斯(Garett Jones)呼吁“减少10%的民主”,但这些东西无法衡量。目前来说,提出上文所述的原则就足够了。我们没有义务捍卫现状,也没有义务向强人致敬。如果民主为了生存而收缩,这不会是第一次。
译者/裴伴
来源:美联社